首頁>書畫>人物
何多苓:我不寫詩,但以詩入畫
何多苓,一個中國當代油畫史繞不開的名字。其創作于1981年的處女作《春風已經蘇醒》,以詩句命名,是傷痕美術的代表作之一。詩歌對于何多苓來說,是愛人,是朋友,是生活,是靈感。他說,我不寫詩,但我看詩時,會有畫面感,進而轉化成畫作。

何多苓
目前正在上海龍美術館(西岸館)舉辦的何多苓大型個展“草·色”,主題和策展是由詩人朋友朱朱擬定,匯集了他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品70余件(套),及各類文獻,意在呈現藝術家于漫長的時間跨度之中的獨特脈絡和階段性變化。
草的意象貫穿于何多苓四十余年的藝術創作,“草既平凡如蕓蕓眾生,又充滿蓬勃的生命活力”,這種對比和張力是他的藝術極喜歡表達的。近日,何多苓在接受新華網書畫頻道專訪時說,“草·色”這兩個字概括我的畫作是合適、簡潔的。

何多苓接受新華網書畫頻道專訪
【草色】草對我來說是一種象征
袁思陶:這次帶來上海龍美術館的個展主題是“草·色”,表達了您何種心境?

何多苓個展海報
何多苓:“草·色”是由策展人朱朱起的,我覺得這名字還挺好的,因為“草·色”中的“草”一個是中國傳統詩歌的意境,中國傳統詩歌里有很多提到草的;另一是對我來說,草是一個線索,我的成名作《春風已經蘇醒》畫了一片草地,后來草地又經常在我的畫面中有不同形式的出現。草對我來說有一種意義,代表自然界,一個最普通、最常見的生物,它生長的面積大、密度大,在春天被喚醒,在冬天又枯黃。我覺得,草對我來說是一種象征。它象征著自然界、生命力,而且是一種看似很卑微的生命,但實際上是極其頑強的。這只是一方面,草的意義可能還會更廣一些。
而“色”,我覺得朱朱想表達的,一是考慮到畫草的顏色、畫面的顏色和色調,因為我比較喜歡用一種灰色調來表達我的情緒。另一可能是因為朱朱覺得我比較喜歡畫女性。所以我覺得用“草·色”這兩個字概括我的畫作是比較合適、簡潔的。

《春風已經蘇醒》 何多苓 1981年 96×130cm 布面油畫
中國美術館藏
袁思陶:您從出道開始,傳達的藝術語言是唯美的、優雅的、神秘的,區別于同時代很多藝術家的審美格調。您在審美上追求的是什么?
何多苓:這一點從我20多歲就開始了。我當時在彝族地區的一個大山里下鄉,跟自然有著原始、深度地接觸。這種接觸再回到城市后就不可能了。當時,我把自己當成自然的一個部分,當成森林、大山的一個部分。因為當時的彝族地區是一個多神教的地區,比如崇拜火、動物,會舉辦火把節等,我對這一切都感到神秘,不是不可理解。它本身帶有一種從遠古而來的氣息,這是我一直所迷戀的。這種神秘感、人與自然的關系,我都覺得很有趣,而且一直貫穿了我的整個繪畫生涯。

《俄羅斯森林(黃金時代)普希金·自由》 何多苓 2017年
200x150cm 布面油畫
【詩歌】詩歌潛在的脈絡在我的畫里一直存在
袁思陶:據了解,從年輕時期開始,您就對詩歌非常迷戀。詩歌伴隨著您的藝術創作。請您講一講詩歌是如何給您的創作帶來靈感的?
何多苓:因為我母親是學中文的,她有很多詩集。有一些古書、絕妙好詞、唐詩,我年輕的時候都帶到鄉下去了。我很喜歡看古詩,后來接受四川一些現代詩人的影響,在八十年代我喜歡看現代詩。看現代詩,從鄉村派、印象派開始,一直到現代派的,看了很多。但是我并不寫詩,我看詩的同時,會產生畫面,有畫面感,進行畫面轉換。我就把因為這首詩產生的畫面,力圖記下來、畫下來。這種關系我覺得實際上是一種轉化,是語言的轉化。文字對于詩歌來說是一個代碼。文字對于詩歌也不是直接表達的意思,它是另有所指的。我的畫也是這樣,當我畫這個形體的時候,我也有所指,也有它背后的東西。這一點跟詩歌是很有共鳴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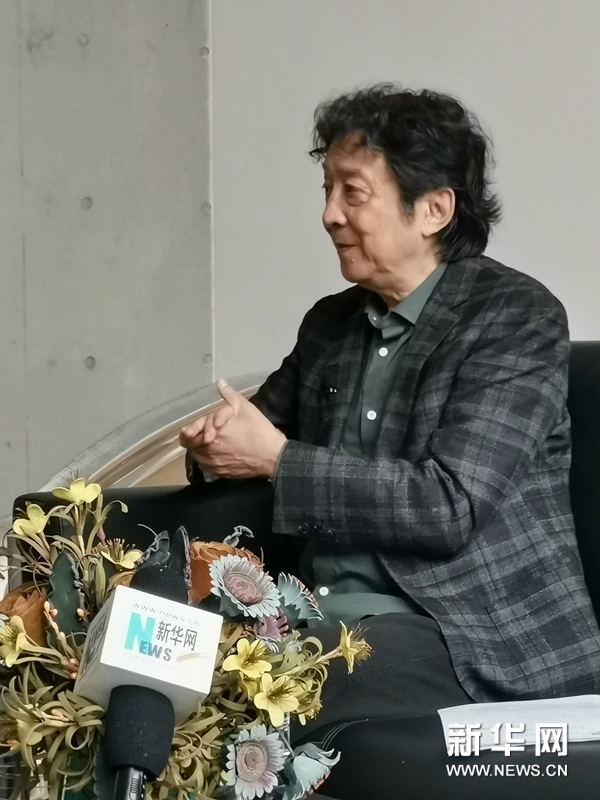
何多苓接受新華網書畫頻道專訪
而在八十年代,我的很多畫作是直接受詩歌影響,像這次展出的《烏鴉是美麗的》《偷走的孩子》,直接用的某首詩歌的意象轉化為一個畫面。現在看起來有些幼稚、不成熟的地方,以后我會把這一點表達得更符合當下我的想法。但是這種詩歌潛在的脈絡會在我的畫里一直存在。我把它看成一種很高級的東西,類似于音樂。

何多苓在創作
袁思陶:您的藝術靈感來源會依賴詩歌嗎?還有別的來源嗎?
何多苓:當然有別的來源。主要來源還是生活、我的觀察、我看到的、我經歷的,但不是具體事件,我把它詩歌化了。比如我在512汶川地震時畫了一些畫,我去過現場,但我并不是去記錄現場,我把現場看的東西加以重新組合,然后用一種詩化的語言來體現,這是我對現實的處理,但是我是用了詩歌的方式把它圖像化了。

《鳥飛絕》 何多苓 2020年
400x450cm 布面油畫
袁思陶:您覺得在創作中,詩歌、現實生活、生命體驗,各自占據了多少比例?
何多苓:生命體驗是最重要的。因為我從事的是一種視覺藝術,我的眼睛直接看到的,加上自己的觀察,去思考,還有閱讀,包括詩歌,但也閱讀別的東西。有些瞬間的意象,偶然的一些圖像,都有很大的意義。還有傳統繪畫,對我的影響也很大。

我一直學習的是西畫,西畫對我的影響很大,我很熟悉西方文化史,自己早就挑選了喜歡的畫家和作品。我后來又關注中國繪畫史,其中的很多東西對我也很有影響。所以,我們現在用的是一個綜合的方法。

何多苓個展現場
【所畫即所得】我用油畫筆“亂涂”,像中國畫“力透紙背”的感覺
袁思陶:比如宋元明清的這些中國傳統山水畫,是不是隨著年齡的增長,在您的繪畫中影響比重越來越多?
何多苓:比重越來越大。雖然我畫的是油畫,但是現在的油畫技法區別于我以前學習的,差別已經很大了,某種意義上可能拓展了油畫的語言。我的油畫語言是經過我的思維和技術雙重轉換之后,尤其跟西方的傳統油畫有很大差別,而且跟西方的現代油畫也有很大差別。

《幽蘭露》 何多苓 2020年
200x600cm 布面油畫
袁思陶:您講一講在中國傳統山水畫家中,比較喜歡誰?
何多苓:比如倪瓚的山水畫,這個是我從小就喜歡的。后來又喜歡宋徽宗時期的院體花鳥畫,我對這些很入迷。慢慢又開始喜歡上文人畫、寫意的繪畫。一直到明清,我現在特別喜歡徐渭的畫法,他狂放的筆法,是他思想的直接體現,比如他的線條,那些像枯草一樣的線條,畫得非常抽象,表達非常精彩。尤其是脫離畫面的線條,令我特別入迷,我覺得這是他內心一種很狂放的表達。
在我的油畫中,我用油畫筆“亂涂”,有些時候像中國畫“力透紙背”的感覺。我正在努力地朝這個方向走,試圖把自己的想法、畫法和畫面完全融為一體,就是“所畫即所得”。

何多苓個展現場
【存在意義】架上繪畫會一直存在下去,不會真正消亡
袁思陶:您這一代油畫家的成長與國家的發展、社會的變遷,有著有重大的聯系。您個人的發展過程中,對自己的藝術語言明確得比較早。很早就有自己的一個追求。
何多苓:我自己的心性、學習、知識結構、時代背景,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的,不可分割。

袁思陶:現在新媒體發展很快,新的藝術形式非常豐富,架上繪畫現在受到來自信息時代各種沖擊。您怎么看待油畫的存在意義?
何多苓:對這個話題我們前一陣還討論過,我覺得非常有趣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時代背景、媒介,這個媒介原來就是紙和筆,后來的媒介就是電腦,現在變成智能手機和網絡。(現在的年輕人)他們用別的媒體來進行創作是非常自然的,甚至是一種必然。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用手去畫畫,他的關注點一定會不一樣的,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
我也很愿意跟年輕人進行這種交流,這種交流不帶有是非、好壞的評價。所謂的好,就是對作品而言,你的這件作品做得好不好。我喜歡畫畫,我就畫畫,你喜歡影像,就用影像。
架上繪畫有它存在的意義,因為還有人需要它。比如人家里掛的畫,博物館里掛的畫,這種作為人手工的一個產物,是非常可貴的,是人直接用腦和手跟自然的一種對話、一種精神的表達。這是最直接的,所以我覺得它會一直存在下去,不會真正消亡的。

《第三代人》 何多苓、艾軒合作 1984年
布面油畫 180x190cm 私人收藏
袁思陶:您覺得自己的藝術能對社會和年輕人產生什么樣的影響?
何多苓:我希望大家喜歡我的畫,能夠理解我為什么這樣畫。我的畫呈現出來之后,希望大家有各自的評價,用各自的角度進入我的畫里,看到他們想看到的東西。不一定是我想表達的,也可能是他們想看到的東西。因為畫掛出來之后,它就跟我實際上沒有關系了。

畫家何多苓與新華網書畫頻道主編袁思陶合影
袁思陶:您在創作一幅作品的時候,有沒有像導演一樣事先設計好?
何多苓:當然是有的。畫畫的時候肯定是自己構思一個畫面,或者是從哪得到一個偶然的意向,偶然的一種啟發或一個靈感,你想畫這么一幅畫。為了畫這幅畫,先收集資料,然后整合成一個畫面,最后把它畫出來。這個過程很復雜,時間很長。但是這些過程不一定需要我的觀眾都看到。當然,我希望我的心路歷程和時間都被觀眾看出來,但是看不出來,或者他看成別的東西都沒有關系的。畫家沒有辦法指導觀眾看自己的畫。我希望他們喜歡,哪怕是完全相反的結論。這是沒有關系的,因為畫家是不能控制別人怎么看你的畫的。
編輯:胡益寧
關鍵詞:詩歌 苓: 油畫


